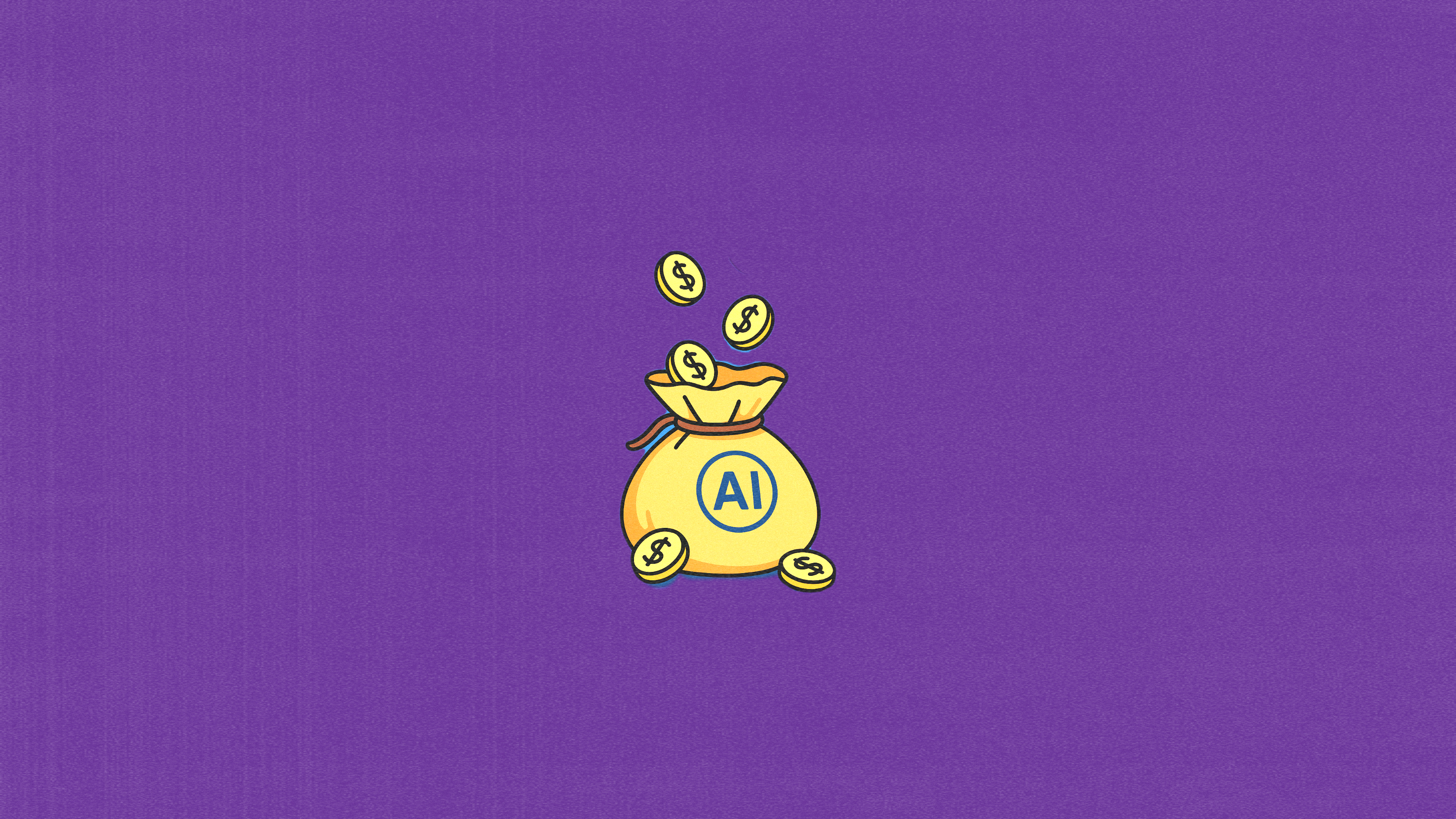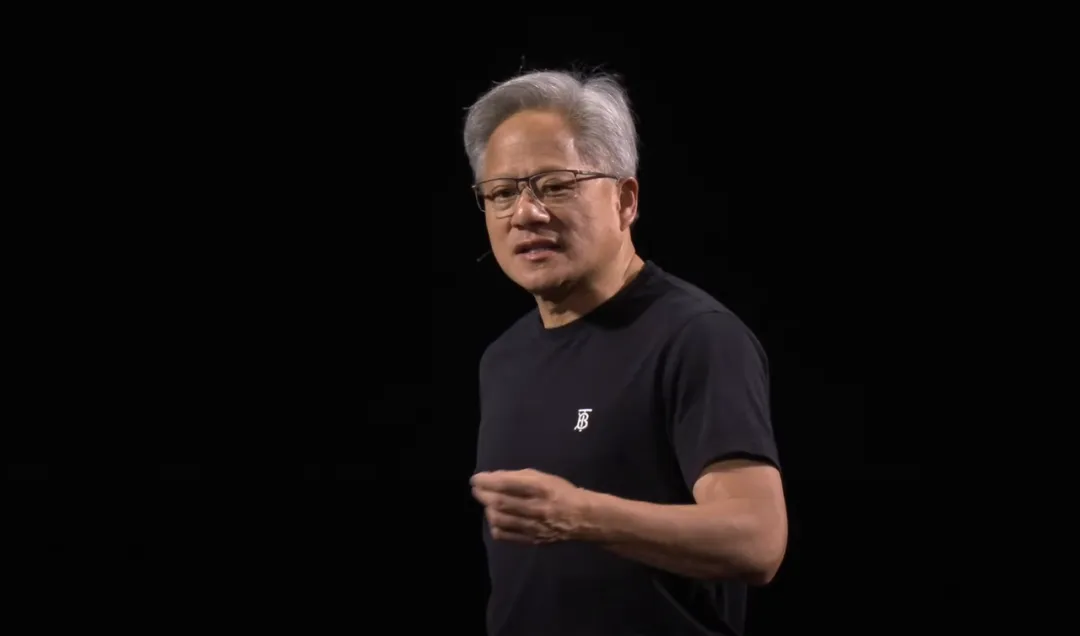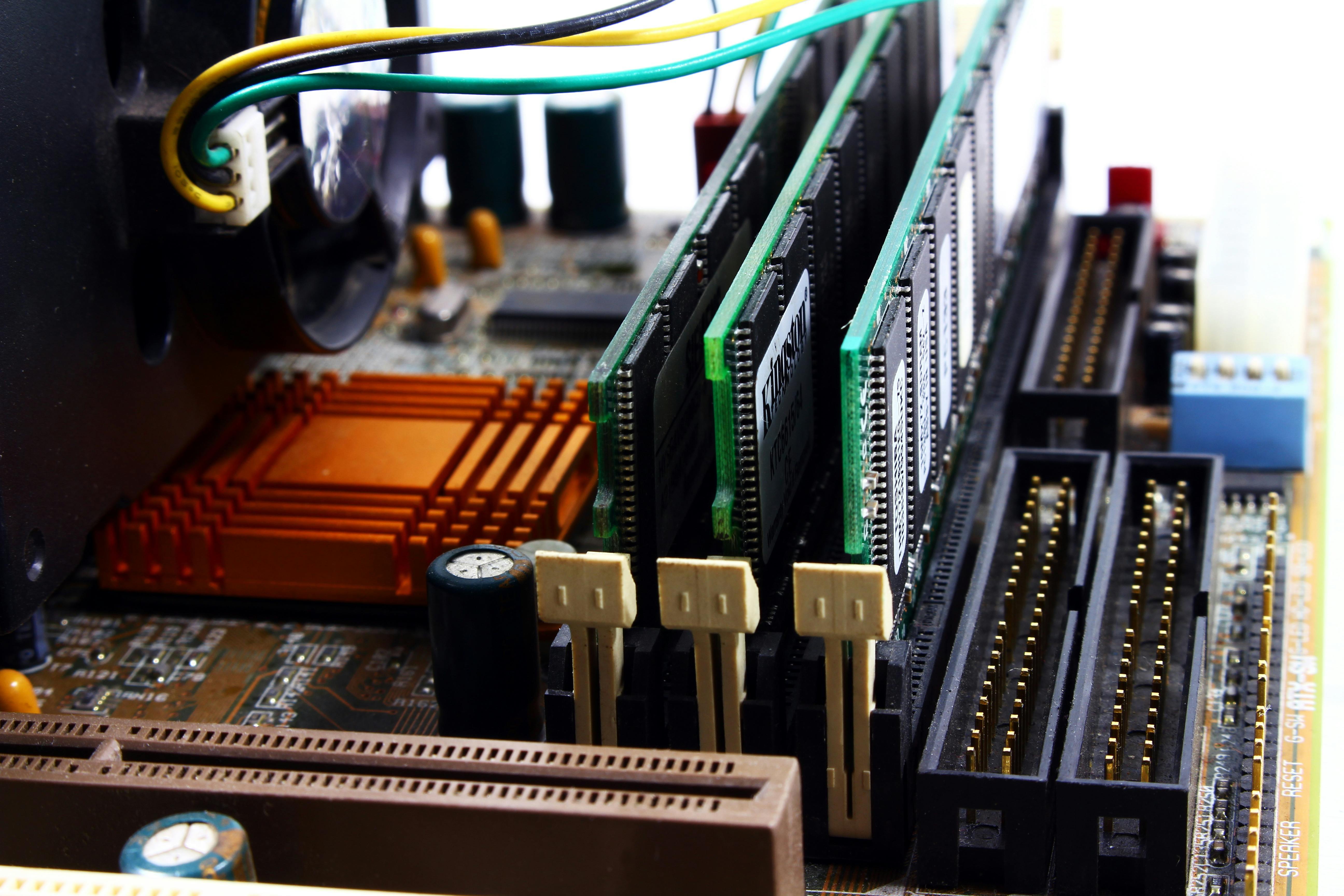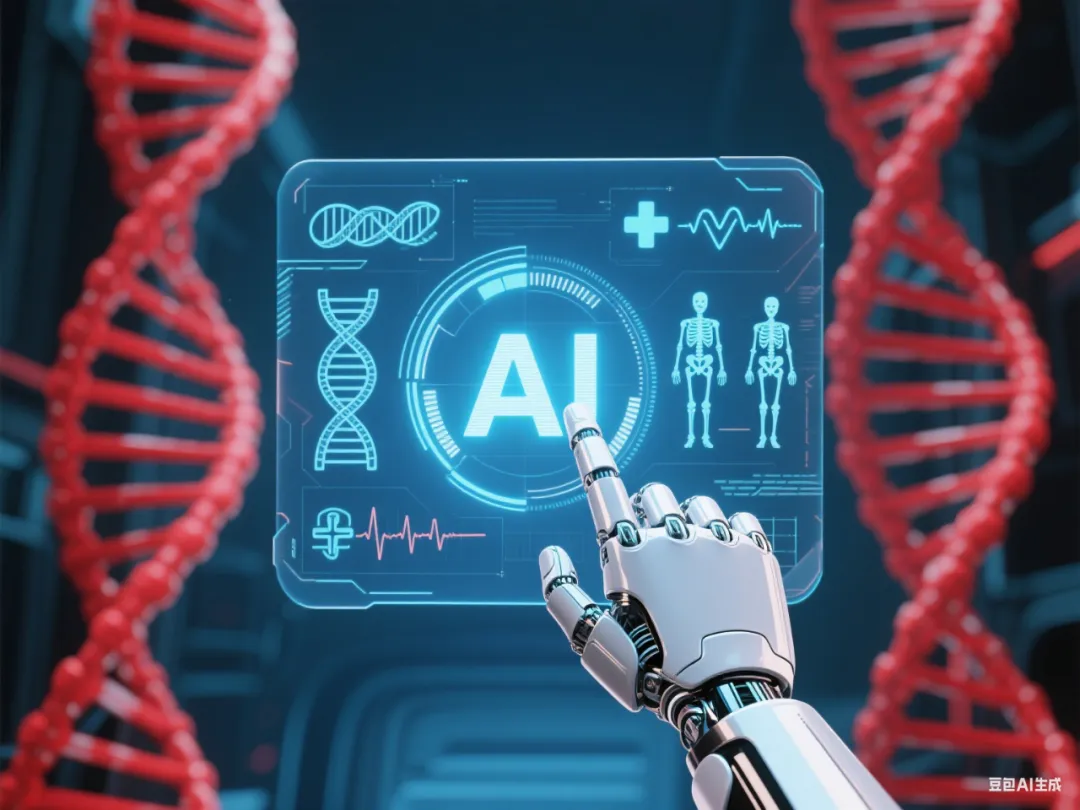AI创业公司出海架构的新趋势:利润中心与成本中心相分离(下)
HelloKitty • 2025-09-24 15:18
577
本文由 逍遥法外夏洛克 撰写/授权提供,转载请注明原出处。
以下文章来源于:逍遥法外夏洛克
作者:夏洛克
大家好,我是夏洛克。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聊了聊“利润中心与成本中心相分离”的架构模式主要是基于怎样的考量而设 立的;在本文中,我们来分析下具体的模式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目前这种架构主要有两种模式,各有优劣,适用不同的情形。
1. 红筹架构
一种是传统的红筹架构(包括直接红筹和 VIE 架构),海外的核心主体会回到境内下设一个 WFOE 或者 VIE 公司,将整个集团公司连接在一起。
这种方式也是相对最常见的一种选择。中国籍创始团队通过办理外汇 37 号文的返程投资备案,在境外合规持有股权(通常是 BVI 主体或者开曼主体),再通过一系列中间架构后返程回到国内设立境内子公司(或通过 VIE 协议控制)。
一方面,公司可通过海外主体完成产品融资、利润归集、海外融资与上市,另一方面,境内子公司可以帮助公司完全承担成本中心的功能。
和过去的红筹结构相比,其业务重心有所转移:
过去红筹结构是为了满足外商投资中国境内限制外资投资的项目,其业务重心本质还是在国内,核心资产都在境内子公司,海外架构都只是为了持股、节税或者隐名性的目的;而现在,AI初创企业出海则将其业务重心转向国内,核心资产在海外结构中,境内子公司反而成为了那个“可有可无”的成本中心。
这种变化其实也反映出中国从 FDI 时代(外商来华投资)走向 ODI 时代(中企出海),不过传统的股权架构可能还并没有跟上时代发展。
举例而言,FDI 时代下的传统 VIE 架构是为解决外资通过非股权的形式控制境内企业;但在 ODI 时代,还并没有一个成熟解决机制来帮助境内公司通过非股权的形式来控制海外企业——尽管最近几年已经有不少企业开始尝试“反向 VIE”模式,但其存在的风险尚未得到市场检验。这一点我们会在后续的文章中再作展开。
这种传统红筹架构的方式的优势在于合规性以及资金跨境流转的便捷性,只要其中国籍股东顺利办理完成 37 号文登记。但这也同时也可能成为最大的卡点。
对于一些正在高速扩张的早期 AI 创业公司,可能存在若干因素让他们不愿意或难以及时去办理 37 号文,例如:
1. 合规瑕疵与治理代价
早期高速发展阶段可能已经存在了一些合规瑕疵,如果要去办理 37 号文登记,会需要花大代价先去治理,这对于瞬息万变的 AI 赛道创业公司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早期投资人的配合程度
一些初创企业的上层并不仅仅有创始团队,可能有其他早期投资人,比如创始人的同学、亲朋或者合作伙伴。这些人(如果是中国籍的话)愿不愿意配合创始人一起去办理 37 号文,也会是一个不可控因素。
3. 37号文本身的办理难度
37 号文本身的办理难度不小,各地经办窗口的指导意见也可能各不相同。以北京和上海为例,37 号文的实操要求在不断收紧,有时候可能一个地方刚开始办,发现政策收紧,短时间内难以办出来,只能重新去另一个城市办理。这里的时间、精力成本都需要消耗。
4. “国际化”问题
传统红筹架构仍然会需要通过 37 号文在境内留下一个子公司,这对于业务重心全部在海外并致力于”国际化“的创业公司来说,就像是留下了一个小尾巴。有创始人就曾向笔者表示,希望尽可能弱化公司的国籍背景,而这个拖在境内的子公司可能会在海外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2. 平行架构
基于上述各种原因,另外一种更激进的架构选择是平行架构。
这种架构从股权上切断境内外的联系,变成平行的一套纯境外结构与一套纯境内架构。
境外结构和传统红筹结构类似,搭建有开曼持股主体、BVI主体、香港主体、新加坡主体等其他企业海外业务需要涉及的当地子公司,但并不会通过这些境外主体“返程”回到境内设立子公司;而境内结构一般由创始人或其信任的其他境内人士代为持有股权,一般根据境内的人员配置和成本发生情况灵活设立这些境内公司。
这样处理看起来既满足保留境内成本中心的优势,也避开上述诸多问题。不过,甘蔗没有两头甜,这种形式也带来的新的问题。
1. 平行架构之间的控制力度问题
两套架构,到底该怎么保证控制力度?在初创草莽时期,创始人可能会选择找人代持境内主体的股权,但随着企业做大,引入外部投资机构,这种粗糙的架构很难令各方满意。
那是否可以引入 VIE 的协议控制形式?
问题仍然存在。由于传统 VIE 协议是两个中国境内主体之间签署(一家 WFOE 与一家 VIE 公司),而此时的平行架构之间即便要签署,也是有一个境外公司与境内公司之间签署,这对于 VIE 协议的跨境可执行性、法域与管辖等都会提出新的挑战。
2. 合规性问题
不办理 37 号文登记,到底是不是合规的?
严格来说,很难直接认为这种情况下创始人在海外持股但不进行 37 号文登记就是违规的,因为 37 号文登记确实只是针对于”返程投资“的情形,如果不存在返程的境内子公司,那即便想要办理,大概率也会被主管部门告知无法办理 37 号文登记。
但这不代表创始团队可以钻空子任意在海外持股,尤其是如果未来要上市,则当下遗留的这个 37 号问题就可能成为上市的实质性合规瑕疵。
3. 资金流转问题
现在银行在审核跨境资金流动的时候都非常非常谨慎和严格,只要发现境外公司上层存在中国籍个人,都会要求提供 37 号文登记,否则不予办理资金流转。这意味着集团公司内想要从海外调拨资金给境内成本中心存在障碍,需要考虑其他支付路径,而越曲折的路径就越有可能产生外汇风险与额外成本。
4. 企业产品规划方向
尽管企业目前是面向海外市场,那会不会未来在海外站稳之后选择回到国内市场开拓?如果是的话,该怎么保证其合规性?37 号文的办理属于”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一旦当下选择不办理,那未来补办非常费劲,向外汇监管部门的解释成本也会非常高。
5. 员工的激励方式与绑定力度
在平行架构模式下,公司的大部分员工(甚至所有员工)都会在境内成本中心下,而由于上文提到的平行架构之间的控制力问题,会导致拥有核心资产的境外主体实际上对公司员工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与约束力度。
这就可能导致几个问题。比如保密性、竞业问题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员工的保密协议、竞业协议与知识产权归属协议与义务都是对境内公司作出的,严格来说与境外主体并无联系,那如何保障公司境外运营主体的相应权益呢?
上述几个问题是平行架构所面临的最核心的几个问题,基于笔者目前的实操经验来看,是存在一些“补丁”来应对这些问题。受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但可以基于下述一些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从投资机构的角度来看,如何退出的重要性更高了。在企业可能存在上市障碍的假定下,投资机构该把投资回报押注在哪个方式上,是稳定吃分红,还是中途转老股离场,亦或是寻求被第三方并购从而退出的机会?
比如,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否有其他可以合法合规满足两套架构的控制力度与资金流转的方式,如果有的话,这套方式是否需要额外的成本或者资金损耗,落地的可执行性如何,企业是否愿意(长期)承担这样的成本?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平行架构模式更多出现在公司创立早期,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架构,在企业发展稳定之后可能仍然需要考虑在适当时候重组,以便解决上述问题。
而从整体 AI 赛道的投融资来看,AI 创业领域整体都还处在早期阶段,技术和业务模式都还没有收敛,没有一条完全成功的范式(好比苹果手机之于智能手机行业,如今的互联网大厂之于互联网行业)。也因此,在企业选择其出海架构与合规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需要不断随着整个 AI 赛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解决方案。



扫码关注公众号
获取更多技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