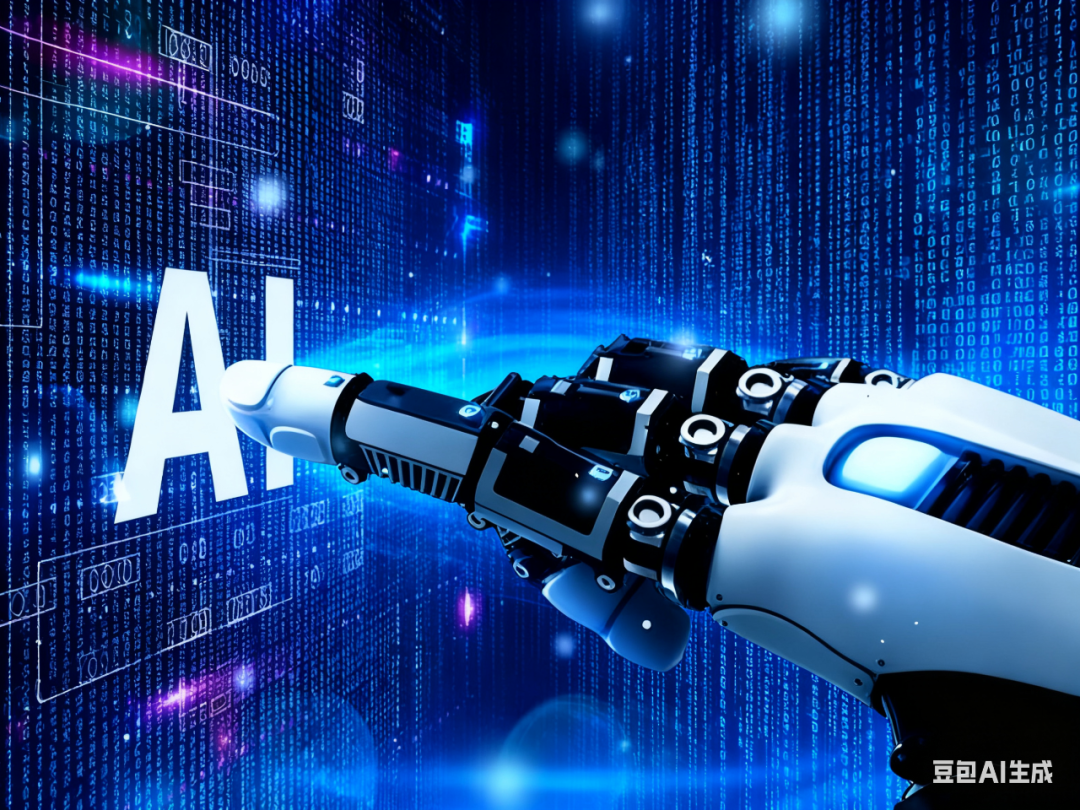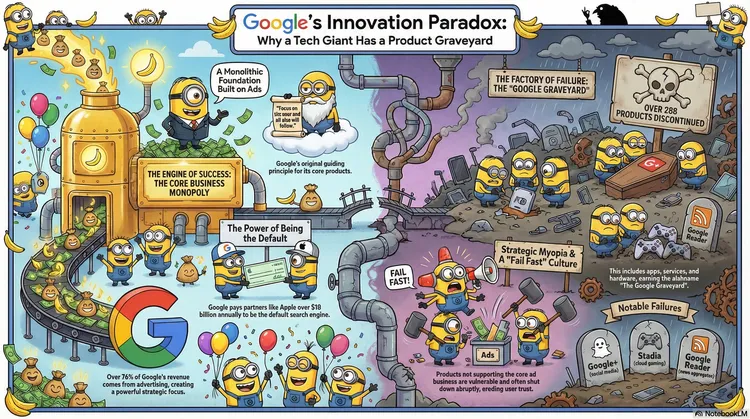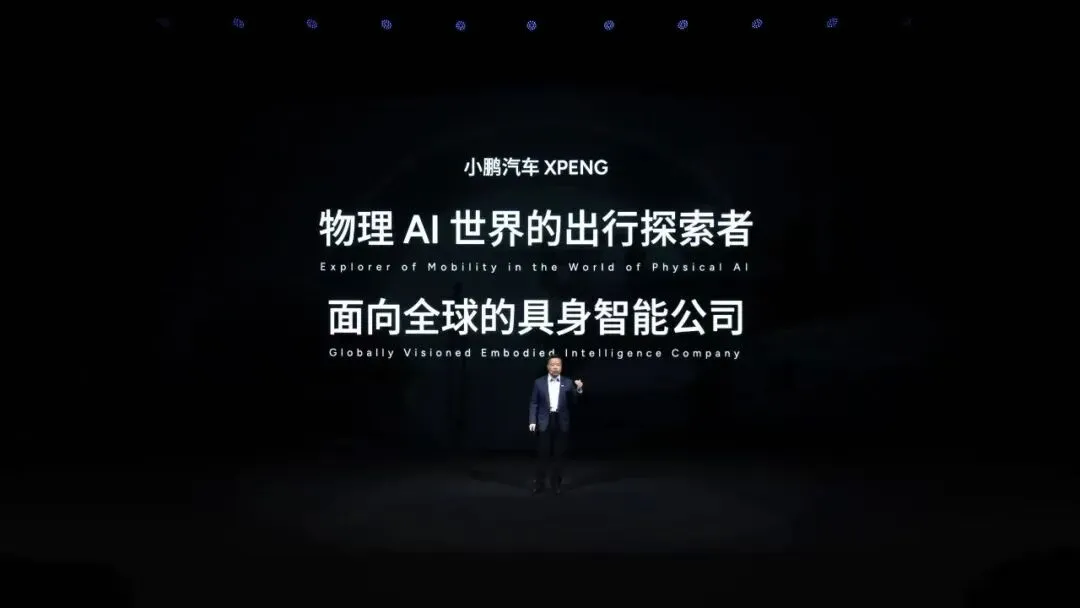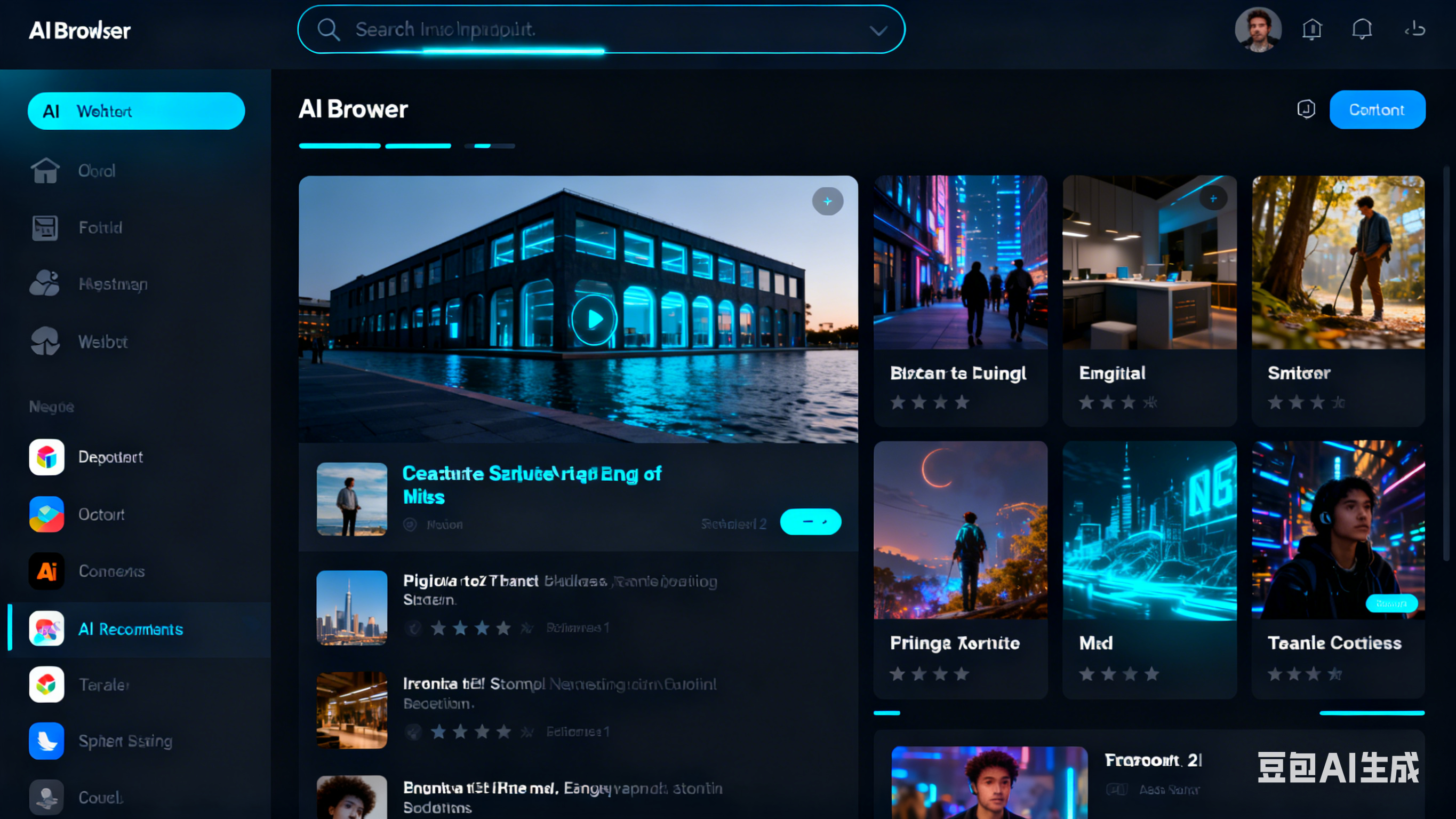OpenAI一年收入都1400亿了,国内AI为啥还是不赚钱?
HelloKitty • 2025-08-11 15:44
2415
本文由 乌鸦智能说 撰写/授权提供,转载请注明原出处。
以下文章来源于:乌鸦智能说
作者:林白
过去一年,Meta 在 AI 上的出手堪称疯狂:斥资百亿收购 Scale AI 49% 股份、砸下上亿美元挖人补强团队,还任命年仅 26 岁的 Alexandr Wang 为 Meta 首任“首席 AI 官”。
按今年的预测,Meta 的资本支出强度达到了惊人的 35% 收入占比。也就是说,每 100 美元收入,就要拿出 35 美元砸进 AI,几乎压上了自己的大部分家底。
像 Meta 这样“豪赌 AI”的公司,在美国还有三家:微软、谷歌、亚马逊。
根据这四大科技巨头公布的财报预测,今年它们在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将高达 4000 亿美元,主要投向 AI 基础设施建设。
这个数字,比整个欧盟 2023 年一整年的国防开支还多,也正在彻底甩开我们。
即使考虑未上市公司如字节等等,加上承担基础任务的运营商 AI 资本开支,根据中金估计,2025 年国内 AI 整体资本开支也不会超过 5000 亿人民币。
很多人把两者差距归因于“算力瓶颈”。但问题的根本,不只是有没有 GPU,而是:有没有一个足够明确的商业逻辑,能撑起万亿级别的投入。
美国已经快速找到了这个逻辑。
从数据上看,美国 AI 赚钱速度越来越快了。OpenAI+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将在今年底突破 290 亿美元,投行预计到 2026 年底,这一数字或将上升至 600-1000 亿美元。初创公司主导的 AI 应用也在 C 端、B 端全面开花。
反观国内,AI 商业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哪怕是可灵 AI 这样跑出来的产品,70% 以上的营收也来自海外。
更严峻的是,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下,原本诞生于中国的 AI 创新正加速“外溢”。Manus、Lovart、Heygen 等公司,或将总部迁往新加坡、美国,或干脆在海外成立公司。
这些外迁的动作,并不只是为了“更接近海外市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国内难以跑通的商业路径,正在压低资本开支的回报预期。
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国内的科技公司正面临日益增长的结构性壁垒。即便撇开芯片限制不谈,如果 AI 商业化路径迟迟跑不通,资本开支的回报率就难以建立。而一旦回报率持续走低,我们在 AI 赛道上与美国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只赚吆喝不赚钱,或许才是我们 AI 产业表面“繁荣”背后最大的隐忧。
全球 AI 赚钱越来越快了
AI 赚钱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过去一年,最惊人的不是 AI 模型的更新速度,而是它带来的商业变现斜率。
先看头部选手:
去年底,OpenAI 年化收入(ARR)是 55 亿美元,今年 6 月突破 100 亿美元,最近《纽约时报》披露,其收入已经达到 120–130 亿美元年化收入,年底将达到 200 亿美元,增幅接近 300%。
Anthropic 的增长更加夸张。Anthropic 去年 ARR 仅 10 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达到 40 亿,年底预计将突破 90 亿美元,同比暴增 800%。
也就是说,到今年年底,OpenAI+Anthropic 的合计 ARR 将达到 290 亿美元。投行预计,按这个速度增长,到 2026 年年底这一数字可能攀升至 600-1000 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亚马逊的云计算业务 AWS 去年全年收入是 1076 亿美元——两家头部大模型厂商花了 3 年就几乎重造了一个 AWS。
而这场爆发,并不只存在于基础模型层。在应用端,无论是面向消费者(C 端)还是企业(B 端),美国 AI 市场都跑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收入曲线。
在 C 端市场,以 AI 编程为代表的初创公司开始爆发:
定价 20 美元/月的 AI 编程 Agent Cursor 的 ARR 已经到达 5 亿美元,吸引了全球超过 36 万用户;AI 编程产品 Lovable 在 2 个月内实现了 1000 万美元收入,并在第 8 个月做到了 1 亿美元的 ARR。
即使小众的 AI 应用,也有不俗的商业化表现。
Tolan 是由 Portola 开发的 AI 伴侣应用,上线仅几个月,年经常性收入(ARR)就达到了 1200 万美元。AI 视频编辑工具 OpusClip ARR 也达到了 2000 万美元。
而 B 端市场,更是成为了 AI 最重要的造富机器,跑出了一批高估值、收入增长迅速的 AI 公司,遍布法律、客服、医疗、招聘等各个领域。
Glean(搜索):估值 72 亿美元,ARR 1 亿
Mercor(招聘):估值 20 亿美元,ARR 1 亿
Crescendo(客服):估值 5 亿美元,ARR 9100 万
Harvey(法律):估值 50 亿美元,ARR 7500 万
Clay(销售):估值 30 亿美元,ARR 3000 万
Abridge(医疗):估值 27.5 亿美元,ARR 1 亿
这些公司的共同特征是:成立不久,收入斜率极陡,产品渗透迅速,估值水涨船高。这种速度,让许多大公司都开始感到焦虑。
大厂打不过小厂”,已成为硅谷近一年来的新共识。原因很简单,这些小厂更加灵活,能在极短时间内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人才也更愿意去创新的环境,而更关键的是,小厂也能拿到融资。
而就在美国 AI 市场沿着商业化路径一路狂飙的同时,我们的 AI 市场则呈现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
技术追平了,但还是很难赚钱
尽管技术层面不断突破,但我们 AI 产业的商业化现实却显得格外冷清。
根据华龙证券的数据,2024 年国内计算机行业 AI 应用板块总营收为 768 亿元,同比增长仅 6.4%;归母净利润为 35 亿元,增幅只有 2.7%。到了 2025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甚至滑落至不足 0.3 亿元,几乎原地踏步。
对比之下,美国 AI 应用公司则跑出了明确的增长曲线:
以 Salesforce、Adobe、ServiceNow、Palantir 等 9 家公司为例,2025 年 Q1 合计营收达 2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1%,平均经营利润率高达 15.8%。
数据背后,是产业结构的根本不同:
美国 AI,是“小厂跑赢大厂”的创业黄金时代,跑出一大批技术型初创公司;
而国内 AI,则是“大厂主导,小厂陪跑”,主流产品几乎都掌握在平台型企业手中。
比如 AI 编程赛道,国内最头部的产品分别来自字节(Trae)、阿里(通义灵码)和百度(文心快码),鲜有独立创业公司崭露头角。
更严峻的问题,即使跑出来的 AI 产品也普遍陷入了“有流量、无收入”的困境。
根据 QuestMobile 数据,截至今年 3 月,国内 AI 原生 App 的月活用户数已达 2.7 亿,甚至超过 ChatGPT 的 1.8 亿。但真正实现规模化变现的产品,寥寥无几。
哪怕是年收入突破 1 亿美元的可灵 AI,70% 以上营收也来自海外市场。
付费困境不仅在 C 端重演,B 端同样难以突围。AI 产品在 To B 市场面临着与 SaaS 企业类似的问题:小企业没预算,大企业靠定制,利润被反复压缩。
一端是用户体量不够,另一端是交付成本过高,真正可规模化、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始终没跑出来。
于是,一大批诞生于我们本土的 AI 创新产品正在外流。
今年 6 月,Manus 宣布,将总部从中国迁往新加坡,并在美国、日本设立分部。原在华团队 120 人中,40 名核心技术骨干随之迁出,其余大部分被裁撤。在此之前,AI 视频公司 Heygen 也将公司总部从深圳迁到了洛杉矶。Lovart 更是直接将公司总部放在了旧金山。
这一轮中美 AI 在商业化上的分野,并非偶然,而是延续了互联网时代早已埋下的路径差异。
入口的逻辑还能讲多久?
2011 年 8 月,Marc Andreessen 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下那句著名预言:“软件正在吞噬世界”,宣告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开启。
从那之后,中美互联网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美国,“软件”接力消费级应用浪潮,推动 SaaS 创业全面爆发。2010 到 2015 年间,每年新增的 SaaS 创业公司超过 1000 家。在这期间,风险投资逐渐达到高峰,每年投入的金额都在百亿美元的级别,这些钱大部分都流入了 SaaS 行业。
而在中国,真正改变时代的却是消费互联网。
字节跳动以信息流重塑全球内容分发逻辑,拼多多则从下沉市场杀出重围,把电商做进了 Amazon 的后花园。每一个成功案例背后,都是超级 App 的崛起与流量入口的掌控。国内的互联网叙事,是流量驱动的一切。
借用公众号“Platform Thinking”的观点,中美的差异不仅仅服务对象的区别,而是两种底层范式的分歧:中国讲“入口”,美国讲“接口”。
其实,我们并非没有企业软件,它们大都存在大厂的「闭环」生态里,作为云计算销售的敲门砖。这些软件表面上做着企业服务的生意,仍未走出消费互联网的影子:靠烧钱换规模、用免费产品堆用户,再靠“流量变现”补血,延续的是典型的「入口」思维。
而正是这种路径依赖,构成了当下的分野:
问题在于,AI 不是一款能装进 App Store 的新应用,它是一种“打散路径、压缩流程”的基础能力。在 AI 的世界里,用户不再从一个 App 出发,而是从问题出发、从意图出发——直接奔向结果。
带来的结果是,入口的价值被不断压缩:从“路径经济”转向“结果经济”,控制用户路径的价值也随之贬值。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 AI 商业化跑得更快:SaaS 公司原本就以“接口”思维运作,AI 只不过是新的能力插件;而在中国,过度依赖“流量闭环”的打法,使得 AI 很难快速嵌入已有的产品与组织流程,反而出现了有技术、无场景,有用户、无收入的尴尬局面。
问题的根源,不在技术落后,而在路径僵化。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我们暂时落后于美国,而是我们仍在用“入口思维”去拥抱一个“接口世界”。
虽然国内 AI 产业在商业化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前景也并未悲观。
技术浪潮的落地方式,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答案。零售、电商、短视频……过去十年中国的每一次产业跃迁,走的都不是美国的那条路。
AI 也一样。它未必颠覆我们“大厂主导”的产业结构,但一定会倒逼所有玩家,从“控制入口”转向“连接接口”:
去争夺流量的起点,不如成为生态的通路;
去封闭用户的路径,不如放大自身被调用的能力。
这,或许才是我们 AI 产业,真正走向商业化的分水岭。



扫码关注公众号
获取更多技术资讯